|
作者: 医院骨科 冯法博孙垂国陈仲强 胸椎管狭窄症多是由于退变性韧带肥厚甚至骨化、椎间盘突出、椎体后缘骨赘、小关节增生等一种或多种病理因素压迫胸脊髓而引起的一组临床症候群,其中胸椎黄韧带骨化(thoracicossificationofligamentumflavum,TOLF)是导致胸椎管狭窄症最常见的原因[1,2,3],在需要手术治疗的由胸椎退行性变引起的胸脊髓病中TOLF可占到51%[4]。 自年Yamaguchi与Fujita[5]报告TOLF引起的胸椎脊髓病以来,TOLF已逐步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但目前其病因与发病机制仍不清楚。由于胸廓的保护作用,胸椎解剖结构相对稳定,胸椎管狭窄所导致的胸脊髓病发病率要明显低于颈椎管狭窄导致的脊髓病或腰椎管狭窄症[6],因此目前对其认识远不如颈、腰椎疾患清晰。一般认为,TOLF是一种病理性的异位骨化,起病隐匿,由于胸脊髓血供较脆弱,当椎管狭窄时可明显影响脊髓血液循环,可造成严重的脊髓功能障碍。鉴于此,TOLF手术风险也相对较高,根据不同的骨化类型,手术治疗有多种方式[7,8,9,10],不同骨科中心所报道的手术有效率和优良率差异较大,优良率多在75%以下[11,12,13,14,15,16],原因之一就在于目前对TOLF的定位诊断仍存在较大困难。 由于TOLF往往合并有胸椎间盘突出或后纵韧带骨化,以及颈椎病、腰椎管狭窄症等脊柱退变性疾病,并且骨化常呈多节段跳跃或多节段连续分布,症状相互叠加,导致其临床表现复杂多样。而且,胸椎管对应脊髓的关系复杂,下胸椎或胸腰段致病时甚至可表现为上下运动神经元混合损害。因此,胸椎管狭窄症常被错误诊断,导致治疗延误[17]。 目前,TOLF的诊断多依赖于症状、体格检查以及胸椎CT、MRI,由于缺乏类似诊断发育性颈椎管狭窄的客观指标,在多节段病例及合并颈腰椎疾患的病例,定位诊断的确立更多依赖于医生的主观判断,导致在制定手术方案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要么减压范围错误或减压范围不足,术后疗效差;要么手术范围过大,导致一系列手术相关并发症,为临床诊治带来一定的困难。 因此,对TOLF临床特点、诊断流程,特别是定位诊断方法的认识尚有待深入探讨。本文就其临床特征、分型及目前临床定位诊断中所面临的问题及进展作一综述。 一、TOLF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好发部位 此前的观点认为,TOLF是一种少见病,主要发生在东亚,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在日本,TOLF手术占全部脊柱外科手术的约0.09%,而需要手术的TOLF患者仅占全部人口的0.6?[4]。但近年来,日韩以外的国家报道TOLF有逐渐增加趋势[18,19,20,21,22,23],特别是在中国,TOLF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手术相关的报道也越来越多[24,25,26,27,28]。来自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提示TOLF在成年人中可能是一种常见表现。Guo等[27]采用MRI及CT对中国南方名志愿者检查,发现TOLF的发生率为3.8%,但无明显的临床症状;Lang等[28]回顾性分析例以胸部症状就诊患者的CT检查结果,重建胸椎后发现63.9%的患者有明确的TOLF,但没有造成明显的椎管狭窄。这说明TOLF真正导致脊髓压迫出现临床症状的患者可能只占其中很少部分,因此明确何种程度及类型的骨化才可能引起脊髓损害是诊断的关键。 多项研究显示[27,28,29],黄韧带骨化最常发生在下胸段(T9~T12),可能是由于这一部位位于胸腰椎的移行处,而且下胸椎较上胸椎骨性胸廓保护薄弱所致。 二、TOLF的临床特征 TOLF临床表现较为复杂。患者多有受累平面以下的感觉及运动功能障碍症状。早期表现为胸背部疼痛、下肢麻木,病程进展时可出现胸部束带感、下肢痉挛性瘫痪表现,累及腰膨大及脊髓圆锥者可有括约肌功能障碍及鞍区感觉障碍[11,30]。在出现以下症状时应高度怀疑TOLF:单侧或双侧下肢的弥漫性麻木、疼痛等感觉异常;单侧或者双侧下肢的无力、沉重感、行走不稳等运动异常;脊髓源性跛行;排尿费力甚至尿失禁。 体格检查时典型的TOLF表现为下肢的上运动神经元损害,如感觉减退甚至消失,肌张力增高,肌力减弱,腱反射亢进,病理征阳性等。需要注意的是:T10~T12节段病变致脊髓圆锥损害时,临床表现可为广泛的下运动神经元性损害,如腱反射消失、肌张力下降等,甚至上、下运动神经元混合性损害,如双下肢的感觉减弱乃至消失[11,30],易与腰椎椎管狭窄症相混淆,临床上需细致鉴别。而TOLF合并脊髓型颈椎病时,由于两者均可导致下肢功能障碍,此时若患者症状以下肢为主,则极易造成漏诊、漏治。应怀疑TOLF的体征包括:上肢功能正常而下肢为上运动神经元损害;下肢呈上、下运动神经元混合性损害。 三、TOLF的影像学特点及相关分型 (一)X线检查 胸椎侧位片上TOLF多表现为椎间孔处钩状或鸟嘴样的占位。可以根据形态不同分型为:棘状型、鸟嘴型、结节型和线样型,其中棘状型最为常见[13]。但是由于受到肩部和肝脏的干扰,X线检查诊断早期TOLF困难。而且胸椎侧位X线片表现类型与骨化的病理类型无一定的对应关系,不能用来判断骨化的成熟程度和对脊髓的压迫程度[31]。 (二)CT 目前临床上以CT及MRI作为诊断TOLF的主要影像学手段,二者多联合应用于TOLF的诊断。 CT可显示TOLF的位置、骨化形态、椎管侵占程度以及是否伴有硬膜的骨化。TOLF在CT横断面上表现为沿椎板或关节囊部的高密度线样影,行矢状位CT重建扫描,往往会发现相邻椎板之间有骨桥的形成。黄韧带骨化和黄韧带肥厚也可以通过CT进行鉴别。CT的优势在于可以轴位逐层扫描,不会遗漏骨化最严重的层面,但CT有时会遗漏多节段病变。目前有多位作者根据CT轴位像上TOLF形态提出多种分型[12,31,32],其中以Sato分型最为常用,最初提出作为胸椎黄韧带骨化CT横截面的形态分型,定义为侧方、延伸、扩大、融合和结节(lateral、extended、enlarged、fused、tuberous)五型(图1)[1,4]。CT分型目前多被用于评估TOLF手术预后情况,但是否与预后相关目前尚存在争议[26,29,33,34,35,36,37]。Sato分型各型骨化的生长位置及椎管侵占程度都不相同,是否与脊髓损害程度相关目前还缺乏研究。若能根据骨化的位置及类型判断脊髓损害的程度,则有望为定位诊断提供帮助。 图1 Sato的胸椎黄韧带骨化症CT分型A侧方型B延伸型C扩大型D融合型E结节型 (三)MRI MRI对骨化形态的显示虽不如CT清晰,但MRI显示病变节段与脊髓信号改变,可以发现CT扫描容易遗漏的多节段病变[38,39],但轴位MRI扫描由于有一定的层厚,无法做到逐层扫描,因此可能会遗漏骨化最为严重的层面。TOLF在T1和T2加权像上均呈低信号,呈球形或鸟嘴样向椎管内突出。而被TOLF所压迫的脊髓则有时会呈现出高信号,在急性脊髓损伤中多被认为是代表水肿、坏死或出血;在慢性脊髓压迫中,脊髓内高信号多代表神经脱髓鞘病变和脊髓内微小的空洞形成[40]。 依照胸椎MRI(T2WI)横断面上黄韧带骨化的形态、大小,可将黄韧带骨化对椎管的侵占程度分为四度[41]。Ⅰ度:黄韧带骨化存在,硬膜囊尚未受压或刚接触。Ⅱ度:硬膜囊受压变形,脊髓未受压。Ⅲ度:硬膜囊受压而局部闭塞,骨化韧带已接触脊髓表面,脊髓未明显受压变形。Ⅳ度:脊髓受压而明显变形(图2)。一般认为:Ⅰ与Ⅱ度骨化未压迫脊髓,不会引起脊髓损害,无需切除减压。Ⅳ度骨化脊髓明显变形,必定会有脊髓受损的临床表现,需要予以切除减压。Ⅲ度骨化的黄韧带接触脊髓,但尚未导致脊髓变形。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患者可能出现较轻的临床症状及体征,而多数患者没有症状;有的属于未成熟型骨化,有的则为成熟型骨化。所以是否需要切除减压还需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 图2 MRI(T2WI)横断面上黄韧带骨化分度AⅠ度BⅡ度CⅢ度DⅣ度 影像学上还根据TOLF所累及的节段数目及分布情况将之分为:局灶型、跳跃型和连续型骨化[32]。Guo等[27]对66名MRI发现有TOLF但无症状的志愿者进行分析发现:45名为局灶型(68.2%),21名为多发节段型(31.8%),而其中11名为连续型,10名为跳跃型。而陈仲强等[15]回顾了82例行手术治疗的TOLF,其中局灶型仅占11.1%,63.0%的病例为连续型,35.4%的病例为跳跃型。可以注意到,无症状TOLF患者与已出现明显脊髓损害需要手术治疗的TOLF患者,TOLF分型的分布明显不同。而不同演变阶段的骨化可以出现在同一病例脊柱的不同部位,这就又提出一个问题:影像学显示的局灶型、跳跃型和连续型骨化分布是TOLF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还是自身特有的不同类型?此方面还缺乏相应的临床研究。 (四)神经电生理检测 目前,肌电图及神经电生理检测广泛应用于脊柱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术中监测及预后研究。体感诱发电位(so-matosensoryevokedpotential,SEP)与运动诱发电位(motorevokedpotential,MEP)多用于颈椎神经根、脊髓以及腰骶神经根的损害,肛门括约肌肌电图多用于检查圆锥损伤,对于胸脊髓损害较少采用电生理的方法。脊髓MEP可以客观反映脊髓的运动传导功能,理论上讲,通过分段检测MEP可以协助判断多节段TOLF压迫脊髓的责任节段,以MEP检查背伸肌[42,43,44,45,46,47]、腹内斜肌[48,49]、肋间肌[49,50],在刺激大脑皮层时,引发肌电反应。然而,MEP检查结果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定位价值有限,目前主要用于定性诊断和术中监测。 四、TOLF诊断所面临的问题及相关进展 临床工作中通过详细的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辅以MRI检查多可快速确诊胸椎管狭窄症,并进而排除胸椎OPLL及TDH,而进一步的胸椎CT轴位平扫和矢状位重建常可确诊TOLF,并清晰显示骨化的形态以及骨化的密度(图3)。 图3 TOLF的诊断流程图 然而TOLF通常累及范围较广,可发生于一至多个节段,甚至累及全胸椎,常呈连续或跳跃性分布,使得目前的定位诊断存在很大困难。临床资料显示局灶型仅占11.0%,连续型和跳跃型分别占53.6%和35.4%[15]。连续型和跳跃型分布的TOLF中,各个骨化节段的脊髓压迫程度常常不同,在临床诊疗中很难准确判定责任节段或各节段分别引起的症状或在全部症状中所占的比例,这为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带来很大的困难。若有方法能准确判定何种程度及类型的的TOLF参与脊髓损害,那么可在保证手术疗效的同时缩小减压范围,降低手术创伤。常合并颈、腰椎退变性疾患也是TOLF的突出特征。Miyakoshi等[13]对45例TOLF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35.6%的患者同时合并脊髓型颈椎病(cervicalspondyloticmyelopathy,CSM)或腰椎间盘突出症。陈仲强等[15]在82例TOLF患者中发现仅是合并CSM或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的患者就达48.8%。腰椎间盘突出症通常表现为神经根损害症状,与胸脊髓受压通常不难鉴别。但胸腰段TOLF由于累及腰膨大或者脊髓圆锥,可表现为上、下运动神经元混合性损害或广泛的下运动神经元损害,需与腰椎疾患细致鉴别。当TOLF合并CSM时,由于两者均可导致下肢的上运动神经元损害,因此若患者症状以下肢为主,则很难确定责任病变位于颈椎还是胸椎。因此,在此类病例中,判断TOLF是否参与脊髓损害同样有助于在去除责任病变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创伤,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 Ono等[51]曾根据病理特点提出韧带骨化分为成熟型与非成熟型。周方和党耕町[52]根据TOLF影像学和病理学上的对照,得出结论:CT的均匀性骨化及MRI上的无信号的骨化对应病理组织学的成熟型骨化,CT的不均匀性骨化及MRI上的低信号、等信号的骨化对应病理组织学的不成熟型骨化。成熟型骨化在临床上属静止型,在压迫不重的情况下,可对其密切随访;而不成熟骨化在临床上属进展型,应予预防性切除(图4)。赵建民和党耕町[32]对手术未切除的TOLF病例进行随访,也验证了上述结论。 图4 未成熟骨化与成熟型骨化的CT及MRI(T2WI)表现ACT显示骨化腹侧不规则,呈毛玻璃样表现,骨化密度不均匀BMRI显示骨化密度与脊髓信号相比为低信号或等信号CCT显示骨化腹侧规则,骨化呈均匀高密度DMRI显示骨化为无信号(黑色) Ogawa等[53]通过对25例单纯胸段脊髓压迫症且将要行手术治疗的患者进行10秒内的踏步试验并对患者行胸段脊髓病的日本骨科学会(JOA)评分与下肢运动功能评分,发现10秒内的踏步次数与患者手术前后的总JOA评分及下肢运动功能评分之间均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认为10秒踏步试验可用于评价胸段脊髓压迫症的严重程度。但此种方法对于胸脊髓损害的定位诊断并没有直接帮助。 孙垂国和陈仲强[54]对35例TOLF合并CSM患者的病史、体征、影像学表现进行研究,发现当CSM患者的JOA脊髓功能评分(满分17分)上肢构成比(上肢功能评分/总分×%)36%时,有72.2%的病例合并TOLF。此方法可作为在合并CSM时,防止漏诊并判断TOLF是否参与脊髓损害的初筛方法,但此方法的缺点是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灵敏度及特异度有待提高,且无法区分多节段TOLF的具体致病节段。 神经电生理检查对神经损害有辅助诊断价值,但对于TOLF的定位诊断价值有限。Nakanishi等[55]通过设立对照组,认为小指展肌与(足母)展肌的中枢传导时间比值有助于区分胸脊髓压迫与颈脊髓压迫:当比值≤0.52时,诊断胸脊髓压迫的比值比为68.4(95%可信区间:8.62~)。Baba等[56]采用脊髓诱发电位技术,将电极置于硬膜外腔,通过特征性的异常波形定位胸椎管狭窄症的病变节段(图5):波形1(波幅下降30%)与波形2(波幅下降介于30%与50%之间)所对应的节段压迫较轻,不认为是责任节段。波形3(波幅下降超过50%)与波形4(负波变为正波)对应的节段脊髓受到明显压迫,认为是引起脊髓损害的责任节段。此方法并非针对TOLF,准确率受检查条件和检查时机的影响较大,缺乏简单直观的量化指标;同时在脊髓附近进行有创操作,本身风险较大。 图5 脊髓诱发电位所产生的四种波形 目前临床上仍主要借助MRI确定TOLF引发脊髓损害的责任节段:如TOLF仅压迫硬膜囊而未压迫脊髓,那么认为其不参与症状发生,可观察随访;如TOLF已致脊髓受压变形,则考虑手术切除。但若是骨化的黄韧带接触脊髓,而尚未造成脊髓的变形,有些患者可能出现较轻的临床表现,而多数人没有症状,此时缺乏量化的指标来判断是否需要切除减压,大多数时取决于医师的临床经验,主观性较大。 国外曾有学者首先提出利用MRI及CT进行胸椎椎管面积及矢状位椎管前后径的测量方法,但仅探讨了二者与TOLF预后的相关性。Sanghvi等[10]利用MRI计算黄韧带骨化侵占下的横断面及矢状位的椎管前后径,以及与正常层面前后径的比值,并与术前JOA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存在相关性。说明椎管侵占程度与神经损害程度相关,但并未进一步计算临界值,对临床指导价值有限。 与MRI相比,CT的优势在于可以轴位逐层扫描,不会遗漏骨化最严重的层面,并且可精确显示骨性结构,定量测量TOLF对椎管空间的侵占程度。刘宁等[57]曾采用病例对照的方法,以CT为基础,测量椎管面积残余率,计算引发脊髓损害的临界值。得出残余率为80%时诊断TOLF参与脊髓损害的灵敏度为93%,特异度为95.5%,诊断符合率为93.8%(图6)。此方法的优点是首先应用CT的方法进行椎管面积测量,提出椎管面积残余率的概念,并设立对照组得出了椎管面积残余率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准确度相对较高。但此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以椎管面积作为测量指标有几个缺点:一是测量面积无法区分骨化位置,同样的残余面积下,双侧骨化与单侧骨化的脊髓压迫程度实则不同,位于椎管中央的压迫和椎管侧方的压迫对于脊髓损害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二是目前国内的PACS影响工作站尚无法直接进行椎管面积的测量(因其为不规则图形),需将影像学资料拍摄照片后再用相关绘图软件进行测量,方法较为繁琐,临床工作中难以广泛开展。 图6 利用CT轴位来测量椎管面积残余率的方法(摘自:刘宁,陈仲强,齐强,等.胸椎黄韧带骨化椎管侵占与神经损害的关系.中华骨科杂志,,27(7):-.)A AB和CD分别为椎管前后径和椎管发育性前后径。EF为椎管横径,等于图B中的E1F1。椎管侧界为经过E、F的垂直线B同一椎体椎弓根平面的椎管横径E1F1C Photoshop套索工具计算OLF侵占下的椎管面积(黄色阴影部分)D椎管发育性面积,即同一椎体椎弓根平面的椎管面积(黄色阴影部分) 目前,针对TOLF合并颈椎病及多节段TOLF的定位诊断,北医三院基于以下的原则:(1)胸椎管狭窄症常合并颈椎病,其诊断和治疗需要紧密结合临床和影像学表现进行分析,脊髓功能评分可以为此鉴别诊断提供帮助[54]。(2)对于上肢症状轻微、下肢症状严重者应首先考虑胸脊髓压迫为主要责任病变,先行胸脊髓减压术;对于上、下肢症状均严重者,可以先行颈脊髓减压术,二期行胸脊髓减压术;但二者间隔不宜过长,建议不超过3个月;对于一般情况好,耐受力好者可以考虑一期完成颈、胸两处减压术,尤其是颈椎病合并上胸椎椎管狭窄者强烈推荐一期手术完成全部狭窄节段的减压[9,16,58]。 在TOLF的具体责任节段的定位诊断方面,椎管侵占程度是目前临床工作中判断责任节段时所能采取的最可靠的方法,以往采用椎管面积测量的方法,存在方法繁琐、不实用的缺点。而北医三院通过回顾性分析44例需手术治疗的TOLF患者与44例无症状TOLF患者的临床资料,在CT片上测量椎管面积残余率[57]、椎管前后径残余率[59]并进行比较,旁正中椎管前后径残余率60%时诊断TOLF引发脊髓损害的灵敏度为95.5%,特异度为95.5%,可为胸椎黄韧带骨化的精确化定位诊断提供参考。 尽管以往的研究对胸椎黄韧带骨化症责任病变的定位诊断有一定的帮助,然而在临床诊疗中具体实施时要么准确性不高,要么比较繁琐,实用性有限,无法为精确化定位诊断提供依据,进而影响术后疗效或造成一系列术后并发症。在北医三院进行的研究中,CT测量旁正中椎管前后径残余率可以准确反映脊髓损害程度,测量方法简便实用,有望成为TOLF定位诊断的辅助方法,但其准确性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来验证(图7)。 图7 北医三院提出的旁正中椎管前后径的测量方法AB为椎管横径,经过AB的垂直线为椎管侧界(即AC,BF),分别在椎管正中线、侧界及二者中线与骨化的交点E、C、D测量椎体后缘到骨化表面的距离作为胸椎OLF侵占下的椎管前后径 五、小结 综上所述,由于TOLF常合并多种病变、多节段狭窄的特征,导致了其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易于误诊、误治或漏诊、漏治。对广泛存在的TOLF或合并后纵韧带骨化、胸椎间盘突出及颈椎病或腰椎管狭窄时,如何界定责任病变或责任节段仍缺乏有效手段。因此,我们需继续研究TOLF影像学表现与临床特点之间的关联,旨在建立一个简单而准确的方法,用于判断TOLF是否参与脊髓损害,在减少手术创伤的同时获得最佳的预后。 参考文献 [1] SatoT,KokubunS,TanakaY,etal.ThoracicmyelopathyintheJapanese:epidemiologicalandclinicalobservationsonthecasesinMiyagiPrefecture[J].TohokuJExpMed,,(1):1–11. [2] AizawaT,SatoT,TanakaY,etal.ThoracicmyelopathyinJapan:epidemiologicalretrospectivestudyinMiyagiPrefectureduring15years[J].TohokuJExpMed,,(3):–. [3] HouX,SunC,LiuX,etal.ClinicalfeaturesofthoracicspinalStenosis-associatedmyelopathy:aretrospectiveanalysisofcases[J].JSpinalDisordTech,May26.[Epubaheadofprint] [4] AizawaT,SatoT,SasakiH,etal.Thoracicmyelopathycausedbyossificationoftheligamentumflavum:clinicalfeaturesandsurgicalresultsintheJapanesepopulation[J].JNeurosurgSpine,,5(6):–. [5] YamaguchiMTS,FujitaS.Acaseofossificationoftheligamentumflavumwithspinalcordtumorsymptoms[J].Seikeigeka,,11:. [6] AmatoV,GiannachiL,IraceC,etal.Thoracicspinalstenosisandmyelopathy:reportoftworarecasesandreviewoftheliterature[J].JNeurosurgSci,,56(4):–. [7] 赵华健,雪原,李鹏,等.胸椎黄韧带骨化的病理单元及分层八边手术法[J].中华骨科杂志,,30(11):–. [8] 郝定均,贺宝荣,许正伟,等.椎板薄化分解揭盖法治疗胸椎黄韧带骨化合并脊髓病[J].中华骨科杂志,,30(11):–. [9] 孙垂国,陈仲强,刘晓光,等.胸椎黄韧带骨化症合并脊髓型颈椎病手术方案选择[J].中华骨科杂志,,30(11):–. [10] SanghviAV,ChhabraHS,MascarenhasAA,etal.Thoracicmyelopathyduetoossificationofligamentumflavum:aretrospectiveanalysisofpredictorsofsurgicalou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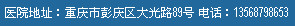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